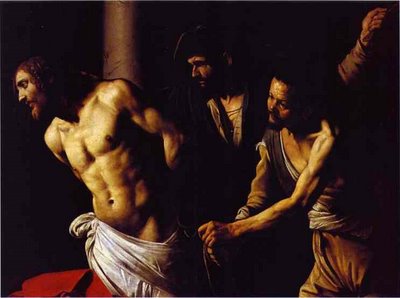一個成熟的心靈應該是有能力同時看待這兩個彼此矛盾的事實:其一,華格納是個大藝術家;其二,華格納是個令人作噁的人。不幸的是,這兩個事實不可單取其一。
〈巴倫波因與華格納禁忌〉,薩伊德
對我來說,二元論,這個事物的相對本質正是音樂根本所在。植根於二元論的奏鳴曲式會成為最完美的藝術表現型式,非僅巧合而已。貝多芬任何一首古典奏鳴曲或交響曲的結構正是以這種二元化的原則為基礎。這個基礎導引出音樂的戲劇性元素,而這就遠不只是大小聲或快慢之分了,因為音樂本身就是戲劇性的,甚至連巴哈作品中比較嚴格的形式亦是如此。常常是這樣:第一主題可能比較英雄氣概,而第二主題就比較抒情性;正是這兩種相對立的元素並存,才賦予音樂以張力和興奮。
《A Music in Life》,第十五章:詮釋,巴倫波因
先來談這本書的第四章,這個樂章主要圍繞在華格納,這似乎是一個永久的爭議性命題,對我而言華格納也是一個永恆的探索的命題。圍繞在華格納週遭的,除了音樂上和他個人性格與行事訾議,更多的是華格納和反猶主義牽扯不完的恩怨。作為一個猶太人,巴倫波因曾因為2001年和柏林國立劇院在耶路撒冷的巡演中演出《崔斯坦與伊索笛》的片斷音樂,掀起猶太社群很激烈的反應,甚至很多猶太族裔視他為叛徒。而他自1981年在拜魯特音樂節指揮《崔斯坦與伊索笛》開始,就成了這個華格納聖地極出色的詮釋者之一,在他的自傳《A Life in Music》,〈歌劇〉這章裡,巴倫波因花了整半章的篇幅談到他在拜魯特和華格納的孫子以及幾位優秀的劇場導演的共事經驗。但是對於華格納與華格納現象則較少著墨。《並行與弔詭》補足了這個闕如。書末收錄了巴倫波因原載於《紐約書評》的〈德國人、猶太人與音樂〉,以及薩伊德所寫的〈巴倫波因與華格納禁忌〉。我把這三個篇幅一起在此討論。
正如篇首所說,這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命題,面對這麼龐大而複雜的命題,並非僅靠一次對談就能獲致答案。但是正如巴倫波因和薩伊德一直在從事的:向對方拋出善意的理解。
和其他章節不同的是,第四章篇尾收錄了對談的哥倫比亞大學現場聽眾的提問,看得出來很多與談者是有備而來,提出來的問題深刻且尖銳,甚至有一位聽眾提到:『在成為猶太人中首屈一指的華格納迷,在拜魯特指揮的過程中,您曾經覺得痛苦、憤怒或尷尬過嗎?』儘管西方世界政治立場和性向等個人隱私的觸探被視為社交的禁忌,但似乎猶太人就是永遠有這樣豁免的權力。
「巴倫波因是個複雜的人」,薩伊德對巴倫波因知之甚深。這位摯友深符薩伊德心目中「他者」的形象。照巴倫波因提到莫札特是「最後的泛歐人士」,他自己也是現今最後符合「泛歐人士」這種身分的少數知識份子。當然如果以演奏和活動範圍來說,很多的音樂家是符合「泛歐人士」最低限度條件的,但在這個身份背後有著更深層的文化認定的問題。為此,有必要回顧一下巴倫波因成長的歷程。巴倫波因誕生於1942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祖父母是俄裔猶太人,1952年巴倫波因的父母決定舉家遷回剛建國不久的以色列。1954年巴倫波因在父母帶領下來到薩爾茲堡隨指揮家Igor Markevich學習指揮,Markevich是巴倫波因音樂生涯很重要的影響者,是他最先發現巴倫波因的指揮天賦並做了關鍵性的建議,才有了這次薩爾茲堡之行。這趟行程另有一個終身影響巴倫波因的人在等待著他,福特萬格勒,這次的會面福特萬格勒曾建議巴倫波因前往歐洲學音樂,當時因為很多外部因素,巴倫波因沒有成行。再福特萬格勒生前的最後歲月這一老一少的忘年之交才又在薩爾茲堡晤面。自此巴倫波因真正展開了以歐洲為舞台的音樂生涯。他和巴黎與北美的音樂界維持密切的合作關係,每年把時間分配給在芝加哥、柏林、巴黎的不同樂團。他常住德國,但是也經常回到色列。